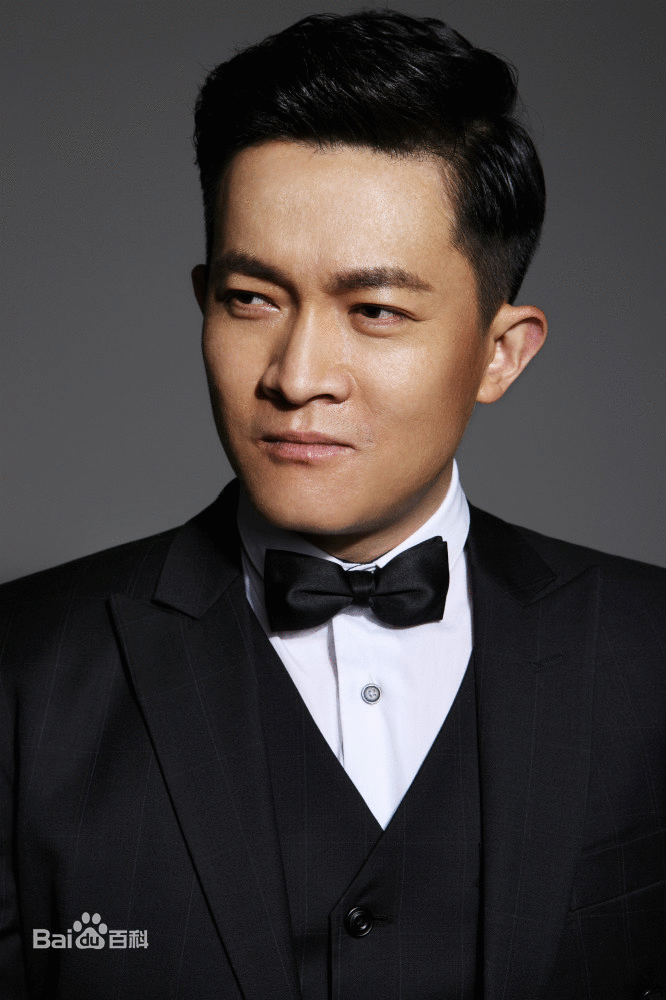通济坊内巷陌幽深,行人稀落,早已不见昔日繁华的影子。苏无名与褚樱桃一踏入坊中,便觉一股冷清之气扑面而来,市肆半掩,门楣蒙尘。二人不敢耽搁,立刻唤来坊正,以卢凌风之名相问坊中豪商住户情形。坊正满脸为难,却也不敢隐瞒,只得道出实情:此处地势偏僻,商贸不振,富贾大户多不肯在此久居;坊中略有声望者,唯有前朝名臣桓彦范旧宅,如今几经转手,终落入商人陈崇之手。此言一出,苏无名心中一沉,隐约察觉一股不祥之兆正悄然酝酿。
与此同时,陈府深处灯火昏黄,祠堂内香烟缭绕。陈崇身着素衣,独自跪在祖先牌位之前,双肩微颤,泪水无声滑落。他抚着案上陈氏族谱,声音哽咽,向列祖列宗倾诉这些年的屈辱与忧惧:身为汉魏名门之后,却无缘入仕,只得转而经商谋生,在士林冷眼与世俗偏见中艰难立足。尤其近来与金光会众人周旋,更令他寝食难安——那些人表面衣冠楚楚,暗里行事卑劣,屡屡干出见不得光的龌龊勾当,使他每一次与之同席,皆仿佛蒙尘祖宗门楣。言及痛处,他一头撞在蒲团上,悲声道自己愧对祖宗清名,死而无颜见之。
祠堂背后阴影中,一道杀气原本悄然凝聚,凶手早已潜伏多时,手中凶器寒光如霜,只待陈崇叩首起身,便欲一击封喉。然而耳中听见的,并非求饶和狡辩,而是一个士族后裔对家门破落的羞惭,对同流合污的憎恶,对金光会行径的由衷不齿。那一声声“有负门楣”,似重锤敲在黑暗中人的心上。凶手指节收紧,又缓缓松开,目光移向供桌上陈氏先祖画像,神色竟隐隐多了几分庄重。他终究收回利刃,向祖先画像郑重叩拜,仿佛在无声告罪,而后轻若幽风地退去,将未竟的杀意留在满室香烟里。
凶手前脚刚走,苏无名与褚樱桃便急匆匆赶到陈府。陈崇仍惊魂未定,听见脚步踏入祠堂,只道是杀手折返,顿时面无人色,失声惊呼求救。慌乱之声很快惊动了街上巡夜的金吾卫,人影、甲响与火光一齐涌入这座原本肃穆的祠堂。卢凌风闻讯赶到,见苏无名竟擅自冒用自己名号,脸色霎时阴沉如水,当众严厉斥责:查案原当循规蹈矩,他却一意孤行,凭一己臆测便冒名行事,若有差池,不仅损及雍州府威信,更有辱狄公清誉。
褚樱桃急得上前分辩,只说苏无名不过一介寒士,无官无衔,若不借卢凌风之名,根本调不动地方吏卒,更别谈夜探坊市、盘问豪商。卢凌风却不为所动,当即屏退裴喜君与褚樱桃,只留苏无名在厅中对峙。他目光炯然,言辞锋利,直指苏无名此番查案,自始至终将怀疑目光牢牢锁定在通济坊与士族门第之上,仿佛凡涉及旧门阀者,便自带罪名,这岂不是出于根深蒂固的偏见?言至激烈处,他更将朝廷科举与士族之争摊开论述:当今进士多长于制艺虚文,只知应试求禄,满腹经纶却未必能理世安民;反观世家子弟,自幼浸润家学,熟悉朝仪礼制,若能痛下决心革除积弊,摒弃骄矜与盘剥之恶,重新振作门风,方可成为稳固社稷、匡扶时政的中坚之力。
这番言语掷地有声,在厅中回响良久。苏无名原本一腔锐气,此刻却难以再逞口舌之快,只得沉默相对。回想昨夜一桩桩线索,他忽然意识到自己确实过于执着于“士族”二字,不自觉间将所有蛛丝马迹朝一个方向牵扯。也许,在真相面前,他并没有想象中那般公正无私。这个念头如针刺般扎在心上,使他不禁放缓了呼吸,暗自反思自己查案之初的偏颇与狭隘。
正当雍州府中暗流涌动,褚樱桃却在心底猛然一惊——昨夜追查鬼市之时,竟将费鸡师遗落在那片人心叵测的阴影之地。她不敢怠慢,连忙拉上裴喜君赶往酥山店寻人。费鸡师虽然怪癖多端,却医术高绝,被寻到时正慢条斯理地啜茶。闻得韦葭疯疾一事,裴喜君恳切相求,他终究还是随二人入府诊病。医者入室,细察脉象与气息,费鸡师眉间虽有讶色,却并不悲观,断言此症并非不治之症,只是缠绵已久,需以针灸长久调理,方有复清明之望。
然而韦家体面观念极重,断不肯让韦葭出门抛头露面。杜橘娘望着病榻上眼神涣散、时而呢喃的女子,心中既怜且恨,怜其身不由己,恨那层层礼法将她推入深渊。权衡再三,她做出一个令众人皆惊的决定——亲自追随费鸡师学习针灸之术,以便日后留在府中为韦葭施针。费鸡师原本只把她当成心善好事之人,谁知不过数次示范,她便能举一反三,记忆不差分毫,下针稳准,天分出众得近乎惊人。老医者眼中精光一闪,当即改口,以谢师之礼受她一拜,将这位女子正式收入门下,自此一脉医术,另启新枝。
从韦府返程途中,褚樱桃心思活络,嘴上更是巧舌如簧,对费鸡师夸赞不绝:一会儿将其医术比作国手华佗,一会儿又称其济世之心足可流芳百世。费鸡师故作冷漠,嘴里嫌她油腔滑调,眼底却明显受用。待她提出再走一趟鬼市,追寻那神秘莫测的松翁踪迹时,他表面连连摆手,实则稍一犹豫,便被她三言两语说动,最终半是不耐半是好奇地应下。就此,一条通往鬼市深处的暗线,又悄悄续了起来。
此时长安城中,暗夜杀机未歇,连日来商贾接连失踪或死于非命,一桩未解,另一桩又起。朝野对此议论纷纷,民心惶惶。卢凌风权衡再三,下令将几起离奇命案并案合查,统一归入雍州府之手。苏无名再度开棺验尸,凭借对尸体创口的细致观察,推断出凶手所用的并非寻常刀剑,而是某种极为锋利的石刃,形制古怪,力道狠辣,却少了金铁器物的痕迹。这一推断,为案件披上了更诡谲的一层面纱。
另一方面,一场看似无关案情的施粮场面,却在城门外悄然上演。安社的施粮队列在晨风中排得极长,米囊堆起小山,只向贫寒百姓与商贾散发,却对前来求粮的士族子弟一概拒之门外。人群中有个家道中落的士族青年,衣衫已补丁累累,却仍挺直脊背。他为了一袋活命的米粮,只得当众否认自己的出身。话音未落,便招来同族子弟的喝骂与拳脚,指斥他辱没宗族,甘为贱民。眼看事态愈演愈烈,一道冷静而威严的声音插入——杜玉现身制止,以自身威望压下纷争。众人退散之后,他却似有所感,提起家中杜氏阀柱新近出土,借机设宴邀约卢凌风,并在席间漫不经心地提及:安社施粮、区分士庶的规矩,皆出自何弼一人之手。
卢凌风心中一凛,随即循线寻至何弼处,与之对谈金光会的来龙去脉。何弼言辞谨慎,却难掩蛛丝马迹,尤其当卢凌风点出连环命案与金光会成员之间的微妙关联时,他眼中那一瞬闪过的慌乱,更让卢凌风确认:凶手选择下手的对象,绝非随意,而是专挑金光会中人,仿佛在有意清算某段隐秘的旧账。
线索渐渐交织成网,卢凌风再度踏入陈府,与陈崇对坐详询那夜情形。陈崇已从惊恐中稍稍平复,回忆起凶手潜伏时微弱脚步,想起黑影一闪而逝时,那柄凶器透出诡异寒意的轮廓,断断续续地描述出其形似石、非金的怪异器形;更在谈话中提及,陈氏与杜、韦两大阀阅,竟皆出自同一旧地,源头相近,枝叶分流。此言如石入深潭,使得案情之中盘根错节的门阀关系,又添几分扑朔迷离。
入夜之后,风过雍州府衙檐角,灯影摇曳。卢凌风暂且放下案卷,特意提点心前往探望裴喜君。屋内灯下,她正凝神描摹韦葭的容颜,笔下那双黯淡而固执的眼睛,仿佛在纸上延续着某种挣扎。卢凌风静静站了一会儿,见她收笔,便问起韦葭往昔。裴喜君轻声道出那段尘封往事:韦葭少年时便嫁入扶风窦氏,夫君仗着门荫入仕,不久便病故,留下她在族中受冷眼;此后,她毅然改嫁长安一位豪商,为此与家族决裂,宁愿抛下门第光环,只求一线自主人生。话音落下,屋中愈发清寂,唯有烛火噼啪作响。
卢凌风听得心中一震,许多此前零散而难以相接的线索,仿佛在此刻被无形的线紧紧牵到了一处。那位长安豪商的身影,缓缓与何弼的名字重叠。他目光沉了下来,隐隐嗅出一股更大的阴谋正在暗处翻涌:金光会、安社施粮、门阀兴衰、商贾接连遇害,这一切,都似被某只看不见的手织成一张巨大罗网。夜色更深,长安城灯火如星,然而在人们看不见的地方,有人正循着那一抹石刃的冷光,悄然逼近真相的边缘。
Powered by 电视指南 http://www.tvzn.com