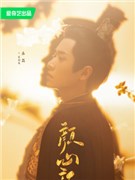相亲失利的一天,朋友开车送文朴回去。车窗外霓虹稀薄,车厢里话锋却不软。文朴数落朋友介绍的女子心术不正,叮嘱他别再插手自己的私事。两人一来一往,嘲讽里藏着关切,像老友间最笨拙的体贴。那段不长不短的路,既是调侃的擂台,也是彼此照看的一方屋檐。
另一边,居委会把易弋叫去。因“日记被公开”的风波,她被要求写检讨。意外的是,居委会还给她指了条路:去夜校教书。她在小小办公室里站着,风从门缝里钻进来,纸张轻颤。复杂心绪里,羞惭与不甘纠缠,但一线新的可能也在悄悄点亮,像旷野里忽然出现的一盏灯。
她推着车回去,在拐角处撞见文朴。易弋诚心道谢,文朴却淡淡一笑,解释这不过是组织的安排。新中国刚立,有些旧伤未平,有些问题未解,但他劝她望向光明,不必耗尽心力于阴影。那番话在激进的年代里,像一束稳妥的光,照拂她将近枯萎的勇气;虽然眼下暗淡,却并非没有出路,未来仍有可期的晴空。
夜校开讲的第一晚,粉笔在黑板上划出细白,易弋刚启唇,座下便有人嚷嚷听不见,她一时慌乱,心里打起鼓点。文朴适时走进来,温声勉励众人:在新的世界里,每个人都该拥有生的尊严,也该拥有追求美好的希望。掌声如潮,震落她心头的尘。曾因日记当众曝光而破碎的自尊,在这几句话里缝合起一角。从那之后,她沉下心,将所学的服装设计拆解成清晰的教案,针脚般细密地铺陈在课堂上,把美与手艺一点点交到夜校学生的掌心。
有时房东张桂花会上门,眼里打着小算盘,悄声怂恿她接私活做衣裳,拿出去卖钱。易弋只是摇头,宁肯清贫,不愿越界。张桂花撇着嘴掉头而去,走廊里回荡一串不以为然的脚步声。生计与操守的角力,在逼仄的屋檐下反复上演,像风筝线拉扯得紧又紧,却还未断裂。
单位里,杨学安一度以激进著称,动辄给人乱扣帽子。幸而每每临到关键,文朴总能扭回错误,替人把不该承受的枷锁取下。可杨学安自己也被急功近利推着走,老母亲病了许久,他竟未抽身探望,直到噩耗来临也未回去见最后一面。与他同办公室的周云清接到老家的电话时哭得肝肠寸断。领导特意批了一个星期的假,他却两三天便匆匆返岗,像被一只看不见的手驱赶着,去追逐那虚无缥缈的“政绩”。
为求功名与飞升,杨学安整日奔走街巷,捕风捉影。先前没能得逞的张桂花心怀怨怼,便栽赃易弋,称她与自己合谋接私活卖衣服,甚至编造出“商业计划”。在彼时敏感的空气里,这样的指控极为凶险。杨学安领人再次搜查易弋的住处,除了那台旧缝纫机,再无他物。无果之下,他又逼张桂花与易弋当面对质。张桂花心虚,却强作镇定,颠倒黑白;几句荒诞的证词,便要把一个清清白白的人推向风口。新麻烦于是压将过来,像雨季里接二连三的雷。
听闻此事的旧友们爱莫能助,只劝她先离开上海避避风头。可这座城市里,有她心之所系的人与未完的牵挂。石库门的影子、夜校的粉笔灰,以及那些目光清澈的年轻学生,都在挽留她。易弋摇头,她要等周肇远归来。哪怕前路布满荆刺,她也要站在自己的位置上守望,像岸边的灯,不为风雨轻易熄灭。
忽有一声“嫂子”自窗外奔来,易弋推窗望去,是小姑子。周云清一路小跑,满脸惊喜地告诉她:周肇远从不是国民党,他早已入党,长期从事地下工作。喜讯如火,她以为重逢在即,飞也似地冲下楼梯。谁料等来的却是另一则消息——几年前他被叛徒出卖,已壮烈牺牲。那一刻,天光忽暗,喜与悲在胸口撞得粉碎,泪水无声坠落成海。可他生前守望的理想,仍像远处不灭的灯,提醒活着的人,别让心中最后的光熄灭;无论时代的风怎样吹,仍要把信念攥在手心,走出属于自己的路。
Powered by 电视指南 http://www.tvzn.com