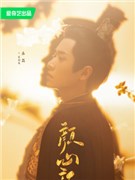雨滂沱,无休无止。易弋伫立在刻着“周肇远”三个字的英雄纪念碑前,像一枚被钉在雨幕里的静默徽章。她不言不语,任由冷雨沿着睫毛汇成细流,滑过脸颊,仿佛迟来五年的回应。五年里,她把日子折叠进衣缝,把想念藏在针脚里,一针一线都缀着名字与约定。终于等到消息,却是一把冰冷的刀,将心口悄无声息划开。文朴不知何时撑伞而至,伞檐泻下细密水线,在两人之间搭起一方无声的庇护。他没有多言,只与她并肩站在风雨之中,像两根倔强却颤抖的芦苇,一起抵御着从天而降的寒凉。
她用近乎恳求的声音问:临别那一刻,他是否痛苦;在献身之前,是否有一瞬动摇。随即又在雨声里呢喃:既然必将把生命交给信仰,为什么还要把婚书递到她掌心,把温柔与誓言编织成一个家的模样?为什么把她独自留在这座灯火万家的城?问题像雨点般杂乱坠落,砸在她心上,无从拾起。曾经,眼前这座城给予她关于未来与幸福的无数幻光,如今光影尽散,连最后的留恋也在忽然的一瞬被抽走,街道的轮廓都显得空洞而遥远。
上级对烈士家属的敬重细致入微,允许她搬回从前熟悉的房间,送来体面的照拂与稳妥的待遇。然而,家具仍旧,气息已换,归居不过是把身影移回旧日的空间,心却再也回不去了。她想离开,回到亲人身边,换一种空气呼吸,于是写下一封出国申请,字字落笔都像在缝一道看不见的伤。把申请交给组织那天,文朴在场,妇女主任言语不耐,误以为她忘了感恩。尴尬之际,文朴用几句平和的话化解僵局,又领她去江边走走。江风带着微咸的凉意,吹散了额前的湿意,行人三三两两,或散步或谈笑,秩序松弛而温良。那一刻,易弋的胸口松了松,像顽结的线头被轻轻理顺。她对着江水低声说,再等等吧,再给自己一点时间,暂时不走了。
周肇远的党员身份公诸于众后,周云清又开始趾高气扬,特意把周肇远的照片放大裱框,端端正正摆在易弋的办公桌上,像一双眼睛,时时端详。更过分的是,他把自己的权力当作放大镜,紧盯她的举动,甚至催促她去夜校开讲,讲他与她的故事,讲那些原本只属于两个人的心事。那晚,她穿一袭绿色旗袍走进教室,衣料在灯光下泛起温润光泽,她打开教案,准备继续教授服装制版与缝制,而台下的周云清絮叨不止,硬要她把私人的悲伤搬上讲台。学生们坐得端正,眼神有同情、好奇与不忍,她把背脊坐得更直,像一条从不肯走形的缝线,仍旧把课程一项项讲下去,不让纷扰撕裂课堂的边缘。
这些年,周肇远不在,傅子和一直以朋友之谊照拂她。他开了服装公司,打理得有声有色,偶遇她的难关总是及时伸手,出谋划策,不作声张。眼下见她步出泥淖,心底也替她生出真诚的高兴。两人寻了个安静角落闲谈,话题跳跃在剪裁、布料与流行色之间,仿佛那些轻快的名词就足以把厚重的阴影压在身后。不想话未过半,傅子和的三位姨太匆匆堵来,眉眼之间刀光雪亮,言辞里酸意翻涌,连番指摘易弋别有用心。易弋哭笑不得,讪讪沉默;傅子和急忙拦阻,压低声音让她先行离开,免得是非缠身。
偏在此时,那位向来泼辣的小姑子站了出来,眼神像一把亮到刺眼的剪刀,利落锋快。她一把拎起酒瓶,瓶身碰在桌沿,发出清脆一响,像是替易弋敲响的守护令。几位姨太原本气势汹汹,见此情景立时心虚,声浪一路低下去,终究不敢再作乱。喧哗散了,空气渐次安静,小姑子回头拍了拍易弋的肩,语气粗直却暖得炙手:有我在,谁也别想欺负自家嫂子。这份不期而至的站台,像冬夜的一盆炭火,把她从被流言挤压的角落里拉了出来。
日子缓缓归于平稳。某个下午,文朴探望她,推门便见她坐在窗前,专注地描画裙摆的线条。她的侧影温柔而坚韧,像一枚被光打磨过的纽扣,安静却有光泽。那一刻,文朴忽然回到初见时的惊艳——同样的沉着,同样的细腻。她见他来,笑意浅浅,亲手为他倒了杯咖啡,热气在指尖袅袅生香。交谈间,他劝她多与同事为伴,多与街坊为友,把话说给人听,把苦放心里化成一朵花。临别时,他递给她一支钢笔,笔身沉稳,笔尖如钩,像一件为她量身定制的小小兵器。你该继续画下去,他说,把心里的图案变成衣裳,把不舍化作针线,让它们在时光里继续走路。
她将那支钢笔在掌心握了握,仿佛握住了某种再出发的暗号。悲伤未必会消退,但可以被编织成新的纹样,藏进衣角与衣襟,让记忆生出温度。而城与江水也像对她有了新的温柔:雨停的黄昏,天空被晚霞轻轻缝合,街灯一盏盏亮起,照见来来往往,又照见她的影子渐渐挺立。她不再急于逃离,愿意在这片熟悉又陌生的土地上,继续把一段段布匹裁成合体的模样,把一份份生活缝合得平整、顺贴。周肇远的名字在碑上,在风里,也在她心口的最深处;至于将来的路,她会用这支笔、用自己的手,慢慢画、慢慢缝,把悲怆化作力量,把爱与信念绣成一幅长长的锦。江风再起,她轻轻闭眼,听见新的日子在水光里,一寸一寸地向前铺展。
Powered by 电视指南 http://www.tvzn.com